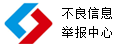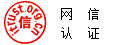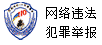财产性判项的履行程度与减刑假释适用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经历了从实践探索上升到制度规定、从单纯考虑财产刑(罚金和没收财产)执行情况到综合判断裁判中涉财产内容执行的发展过程。
关联机制的建立能够激发罪犯履行积极性,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保障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一定程度上解决有财产执行内容之生效裁判“空判”问题,实现了对罪犯服刑改造效果的综合评价,能够更好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也是刑罚变更执行制度更加规范化、精细化的体现,对于实现司法公正、保障监管秩序稳定和罪犯合法权益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对于财产性判项履行程度(即未全部履行)是否影响减刑幅度,以及是否影响假释适用,在历次的司法解释中做了不同规定,实践中也产生不少认识分歧,值得研究。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应用规定》)正式确立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在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司法解释正式提出财产性判项的概念,明确财产性判项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判项以及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责令退赔等涉及财产性质的判项。
《应用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刑”条件的案件,在办理时应当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予假释。至此,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审理关联机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
当时确立的关联情形是,对于减刑适用要综合考察财产性判项,并未明确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即不能减刑或者扣减减刑幅度(实践中一般都要扣减甚至不予提请减刑);而对于假释的适用,则明确规定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予假释。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特殊身份罪犯的关联机制进行了修正。根据《补充规定》第一条,对拒不认罪悔罪的,或者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不予假释,一般不予减刑。本条文针对的是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的减刑、假释。这里明确了特殊身份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程度与减刑假释的直接关联关系。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对关联机制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定。包括明确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的根据,履行能力的判断模式,执行法院与监狱的协助配合工作机制等。
《执行规定》比较好地解决了审判实践中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与财产刑关联制度认识不清晰、标准不统一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执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发现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或者依法由刑罚执行机关撤回减刑、假释建议。这里实际是明确了财产性判项履行程度不再与减刑幅度挂钩,在较早的过程稿中,曾规定财产刑履行程度与减刑幅度直接挂钩,后来考虑到如此规定可能造成履行能力不同的罪犯在减刑处遇上的不平等,因此放弃了该规定,转而将关注点聚焦在履行能力上。
履行程度不应当再作为扣减减刑幅度的因素
尽管《执行规定》对关联机制中财产性判项履行程度与减刑幅度不再进行勾连,但是,基于长期实践惯性导致对该问题仍旧有不同认识。
通常认为,罪犯的财产性判项没有完全履行和已经全部履行应当有所区分。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的,且即使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监狱之间,也会因为履行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报请减刑的幅度。
以H省某地区的三个监狱为例,a监狱规定:对于普通罪犯(即除了“三类罪犯”,下同)达到呈报减刑条件但未完全履行的,一般扣减1个月减刑幅度;数额特别巨大的,根据情况扣减2至3个月的幅度。b监狱规定:对于普通罪犯未完全履行的,履行10%以下的,一般扣减3个月减刑幅度;履行10%至50%的,一般扣减2个月减刑幅度;履行50%至100%的,一般扣减1个月减刑幅度。c监狱规定:对于普通罪犯达到呈报减刑条件但未完全履行的,一般扣减1个月减刑幅度。
显然这种根据财产性判项未完全履行的程度直接扣减减刑幅度是站不住脚的,既造成了执法司法的不公平,也与《执行规定》相违背。
当然,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程度也不是全然没有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程度问题:
应当结合履行能力来判断履行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罪犯的现有财产仅能够履行部分财产性判项,那么,对于罪犯而言,该能够履行的部分就相当于“全部”履行了,毕竟法不强人所难,对于超出罪犯履行能力的部分不应当要求罪犯履行后才能够被减刑,也不能因为罪犯没有能力履行而扣减减刑的幅度。
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的程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实践中的普遍做法,可以将罪犯履行程度作为对罪犯进行限定狱内消费等的参考。毕竟罪犯已然没有进一步履行财产性判项的能力了,在狱内消费方面当然要区别于已经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罪犯。
关联机制的重点是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的判断
根据《执行规定》第3条,罪犯的履行能力应根据财产性判项的实际执行情况,并结合罪犯的财产申报、实际拥有财产情况,以及监狱或看守所内消费、账户余额等予以判断。这里实际上是对罪犯履行能力确定了三个方面的判断因素。
关于财产性判项的实际执行情况。根据《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规定,刑罚执行机关调查罪犯履行能力一般采取向负责执行财产性判项的法院发函的形式,请求原判法院协助调查,但实践中普遍得不到原判法院的配合。因此,为了准确判断罪犯履行能力首先要压实执行法院的责任。
《执行规定》第十三条明确,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收到刑罚执行机关核实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公函后,应当在七日内出具相关证明,已经执行结案的,应当附有关法律文书。需要解决的是,如果执行法院七日内没有回函如何处理呢?有必要作出进一步明确,否则可能因为缺少法院的执行材料而影响对罪犯提请减刑。
关于罪犯财产申报、实际拥有财产情况。采取财产申报措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罪犯申报的自觉性和诚实度,即使在执行机关不断强化教育的情况下,仍有不少罪犯为降低财产申报对减刑假释造成的影响而不如实填报。可以通过审查罪犯户籍地或者居住地相关部门(如县区级民政部门、街道、乡镇、村、社区等)出具的罪犯财产情况或者家庭经济情况的相关证明,了解罪犯家庭及财产情况,同时,也要告知罪犯不履行财产性判项的不利后果,即根据《应用规定》,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直接认定为“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
关于狱内或所内消费、账户余额情况。这类情况比较直观和简单,都是在监狱内形成,由监狱提供不存在太大难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可能存在罪犯故意压低狱内消费的记录或者“借卡消费”的情况,要加强对罪犯狱内消费等情况的调查核实。
上述三个方面的判断(有观点归纳为“三看”判断模式)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同时也要相互印证,综合判断罪犯是否具备履行能力。通过这种判断,对于没有履行全部财产性判项罪犯的履行能力只会得出两种结论,有履行能力而未全部履行和没有履行能力而未全部履行。
而有的观点提出,“对于罪犯履行一定比例或数额的财产性判项,但不能证实确无全部履行能力的,可根据罪犯履行的比例或者数额适当延长罪犯减刑的间隔或扣减相应的减刑幅度”。如何认识该观点提出的“不能证实确无全部履行能力”呢?我们认为,如果通过“三看”判断模式不能证实罪犯确无全部履行能力的,则只能参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罪犯没有履行能力的推定。毕竟,对罪犯是否具备履行能力的判断主体应该是政法机关,而不应当归咎于罪犯。既然推定罪犯确无履行能力了,则不应当再影响到其减刑幅度。